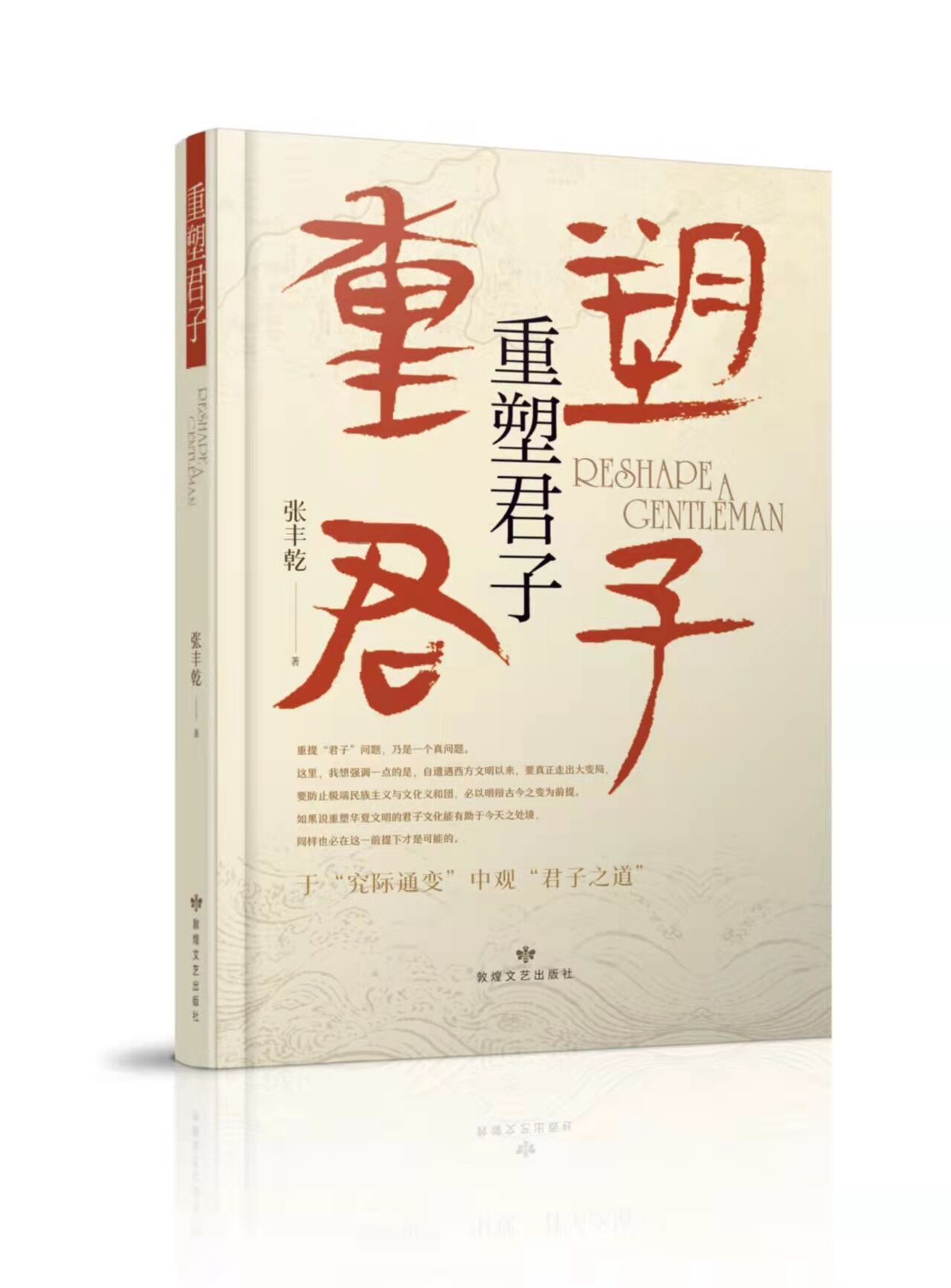
进入近代,中国人自觉发现自己的文明遭遇到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在三千多年的文明史上,华夏文明也一再遭遇撞击:不仅有边疆族群实体不断对华夏文明中心区域的侵蚀与征服,也有来自异域的佛教的挑战。但是,华夏文明主体却并没有认为遭遇什么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为什么呢?
边疆族群对华夏文明中心区域的侵蚀乃至征服,虽然给中心族群带来了动荡,却没有带来文明层面的冲击。因为无论是社会分工的水平,还是生产、生活的技术水准,也无论是社会制度设置的复杂程度与管理水平,还是伦理世界所达到的普遍性阶段以及整个精神世界所达到的高度,都是边疆族群远不及的。在冷兵器时代,更野蛮的族群征服更文明的族群是很常见的历史事件。但是,如果被武力征服的族群所达到的文明程度足够高,其文化具备足够的普遍性,那么征服者通常都会被它所征服的族群的文明所同化。文明族群以其被蛮族征服的方式教化着蛮族,以其等待蛮族开化的方式开辟着普遍性历史。在冷兵器时代,这几乎是一个历史通则。高度文明的希腊(雅典为核心)被马其顿的强大蛮力征服了,但是,崇尚希腊文明的亚历山大不仅把马其顿希腊化,而且推动了他所征服的辽阔帝国希腊化。我们甚至可以说,欧洲的历史从一个侧面看,就是希腊化的历史。而在东亚则演绎着“归汉(华夏文明)史”。无论是匈奴、鲜卑、拓跋,还是女真、满蒙,他们对华夏中心区域的侵扰、征服都以融入华夏文明的方式展开着东亚史。所以,无论面临哪个边疆族群的撞击,华夏文明主体并未将之意识为大变局。
佛教的进入,相对近代西方文明的进入而言,本身不附带强力。它的挑战主要是思想层面。以儒道两家为基底的华夏文明一开始就带着信心与虚心去面对佛教在思想层面所具有的高度与陌异。其中,以道家的“无”格佛家的“空”,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标识着人类最早觉悟到有比“有(色)”更根本的“无(空)”的两个东方文明相遇了,标识着不同于“两希文明”的两大东方文明在究竟处互证到了“空-无”。从此,不仅佛教在汉地获得了不同于其来源地的自我展开的新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家开启了既援道入儒,也援佛入儒的努力,并据此开出了新的胜境——宋明理学和心学,加持了儒家的道统与学脉。由于主要是思想层面的挑战,华夏文明主体能够以开放的胸襟与从容的心态去理解、消化、吸收佛教这种来自异域的异文明,使陌异文明之间的相遇能够以和平、温和的方式展开。可以说,佛教与华夏文明相遇的历史事件是陌异文明以和平方式相遇的一个范例,但很可能也是一个特例。因为从世界史范围看,陌异文明(特别是伟大的文明)之间的相遇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冲突与震荡。两希文明之间的遭遇如此,印西文明之间、中西文明之间、欧美(原住民)文明之间的遭遇也是如此。这里,我们单表中西文明的相遇。
近代遭遇西方文明使中国进入了与遭遇到佛教时完全不一样的处境:首先是,西方文明世界拥有这样一种全新的技术,它完全不同于冷兵器时代那种基于生活实践的技术,而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而基于理论知识的全新技术。因此,这种技术的突破不再是基于生活实践的缓慢积累,而是基于理论知识的不断进展,这一方面加速了技术的持续突破与不断发展,从而在把社会生产水平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的同时,也把社会分工带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化与精细化的加速轨道,另一方面从此也就中止了冷兵器时代“蛮力常可征服文明”这一历史通则。其次,尤其重要的是,这种以科学形态为其重要基础的西方文明在产生出全新技术的同时,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在近代也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自然与人自身的这些全新认识不仅构成了改造自然的基础,也构成建构人类新的社会制度与管理体系的基础。因此,无论是思想世界,还是社会制度与管理机制,都把西方文明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近代面临的挑战,不仅不再是蛮族的蛮力的挑战,也不只是佛教的思想上的挑战,而是全方位的挑战。这是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内涵所在。如何回应这一大变局,是近代以来所有中国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处境性问题。迄今也仍是一个考验中国人之智慧、胸怀与远见的处境性问题。
实际上,在近代,中国人也并非一遇到西方文明就立刻认识到这是全方位挑战的千年变局。所以,他们做出的回应首先是局部性的。
在西方世界的挑战中,新时代的技术挑战是最直接的,因为它最直接地体现为船坚炮利这种强力。这使早期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有识之士也误以为西方文明的强项只在于技术及其所能带来的强力,这种强项被称为“用”。所以,他们试图在维护“体”的前提下展开“用”方面的自强,这就是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宗旨的“洋务运动”。这一运动通过技术-设备引进,官方控股、社会融资,建立了一系列具有现代技术含量的新行业,开启了现代生产方式。在官方带动下,民间资本也开始办“洋务”,在民生领域更新换代,引进新技术。这些努力提供出了新的产品,创造了新的财富,曾一度使大清社会呈现出向上、向好的方向扭转的局面,以致有史家称之为“大清中兴”。但是,误解与误识的代价却是惨重的。
由于只看到西方世界在技术上的殊胜,而误以为华夏文明在“体”方面仍然优胜于西方文明,所以,人们最初也并没认为遇到了千年尺度的大变局。那么,什么是这里所说的“体”呢?相对技术、工具、生产这些被归为“用”而言,所谓“体”至少包括这些方面:1.治理国家层面上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系;2.教化、涵养个人美德与社会良序的伦理体系与伦理机制;3.支撑前二者的形而上思想体系;4.影响甚至塑造着前三者的宗教信仰。由于认为在“体”的这些方面,华夏文明仍优胜于西方,所以,只需通过学习、改善、提高技术这一“蛮力”即可制服“西夷”。时人没有想到的是,西方文明中的技术并非只再是一种“蛮力”,而是基于一种高度理论思维的一种实践配置能力。当然,他们也不会想到,这种全新技术只有在确立起了科学这种思维形态的文化土壤里,才能生根发芽,才能得到持续不断的发展;同时,也只有在新的社会管理体系(包括新的教育体系)下才能得到持续的推动。
他们同样没想到的是,不仅他们直面的西方技术是以关于自然界的理论知识为基础,而且他们尚未直面的西方社会管理体系(包括政治制度)也是建立在关于人类自身的理论认识的基础之上。这种全新的社会管理体系不仅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拥有一种充分激发成员个体的能力与积极性的机制。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他们遭遇到的西方文明世界在经受市场经济、工业化以及启蒙思想运动的多重洗礼之后,其社会伦理体系已经完成了“古今之变”:无论是个人之间、两性之间,还是个人与共同体之间,都确立起了一套经过理性论证或经过理性重估的原则体系。这种完成古今之变的伦理体系不仅超越了血缘-宗族、地域-民族,而且也不再基于传统习俗、宗教信仰,它被自觉为一种普遍的伦理体系。原来出自习俗或宗教的那些具有普遍性的伦理原则被作为出自理性自身的原则纳入了新的伦理体系之中。这种现代的普遍伦理体系既被用来塑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视为构建包括国家在内的共同体的基础。当然,他们最没想到的是,宗教信仰对于他们所遭遇到的西方文明所具有的根本性意义。
由于这些“没想到”,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人们最初做出的因应是局部的。所以,即使没有甲午战争,“洋务运动”这种回应方式也必以其他形式宣告失败。“戊戌维新”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体现出在对真实挑战的认识上迈出了重要一步,那就是承认华夏文明中的“体”(首先就是政治制度乃至伦理体系)也面临着挑战,不得不做出调整与改变。实际上,正是已经强烈意识到自己的“体”至少在政治制度上不仅无优胜之处,相反,相比之下,倒处于拙劣之流,才召唤着革新政治管理制度的变法运动。而以“科学与民主”为其纲目的“新文化运动”则更进一步认定整个文明的“体“都处于劣势:认同民主,则不仅认定了历三千多年之久的帝王政治的落后、拙劣,而且否定了这一传承不绝的帝王政治的合法性;换言之,无论帝王政治多么悠久,也无论它造就过多少辉煌,它都是不再正当的。而当把科学作为一个纲目标举出来,则意味着对缺乏科学传统或者没有产生出科学这种思维形态的文明及其优胜处会产生根本性的怀疑;而当把科学当作理解与认识世界的最高标准或唯一方式时,则必会对文明中所有无法被归入科学形态的那些内容持轻视乃至否定的态度。所以,“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标志着华夏文明主体对自己所遭遇的异文明挑战有了更全面的认知与自觉,但另一方面也开启了通向各种激进主义的闸门。激进的民主通向的是“民粹”,而激进的新文化通向的是反文化。
所以,对挑战性处境的更全面自觉并不意味着就能马上开出更理性、更正确的回应之道。近二百年间,经历了各种反复与曲折,既有光明时代,也有至暗时刻。放长时段看,这乃大文明相遇、交汇会出现的常态,而非我华夏文明独有之不幸。今天,仍值得反思的是:“新文化运动”所达到的处境性认知是否足够全面?它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是否错过了什么?它对华夏文明的反思是否也遗漏了什么?这些问题之所以仍值得反思,是因为此后的处境性回应都与”新文化运动“相关。
实际上,如何更周全地因应遭遇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大变局,迄今仍是一个未了结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回应,都涉及两个相关的老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西方文明?又如何对待华夏文明?
如果我们做个归类,那么在这两个相关问题上,大致可归类如下:一、全盘西化论且全盘否定华夏论。这类激进主张者很少,但造成的实际影响不小。二、全盘西化论,同时不全盘否定华夏传统,如胡适等人为代表。三、不主张全盘西化,也不否定华夏传统,而主张既以现代思想视野重新审视华夏文明,也以之审视西方文明。四、不拒绝西方文明,但主张以温情的态度去理解、对待华夏文明,并力图从中寻出差异性、未来性与优胜处。五、拒绝西方文明,回归或坚守华夏传统。我们可以把第三种主张称为“明古今之变派”,简称“明变派”,把第四种主张称为“温情派”。
张丰乾先生这本书的努力表明,他应介乎“明变派”与温情派“之间。从他提出“重塑君子”的期待可以看出,他相信在华夏文明传统中,有可以补济中国社会在回应大变局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要素。的确,在华夏文明里,君子是教育所要造就的基本目标。我们甚至可以说,华夏文明里的教育事业就是成就君子的事业。“学而优则仕”,并非意味着以“仕”为教与学的目的,而是意味着学而优是仕的前提。何谓学而优?这里的“优”不是科目成绩的一个等级,而是成就为君子。通过学-习而成就为君子,就是学而优。这里所成之君子,不只是一种境界,一种教养,也不只是一种品质,一种风范。儒家教育所要成就的君子乃是这样一种“成人”:他不仅明天下普遍之道,觉世间至善之理,识人间同理之心,且能担此道,行此理,守此心。成了这样的君子,才有资格去配位,才能去仕;当然,这样的“成人-君子”也获得了一种使命:行天下普遍之道-理于天下。如果用现代的话说,那么,君子就是这样有见识有担当的“成人”:认识世间普世之公理,自觉人类普遍之正义,并力行之。简单说,就是为公理而公理,为道义而道义。
实际上,这样的“成人-君子”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人类虽为理性动物而有认识、觉悟普遍公理之能力,但是,人类同时也有致命之弱点:无论个体还是集体,都极易溺于私情、偏于私利而昧于公理与道义。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私情私利与公理、道义之间斗争的历史。前者优胜,则社会必充满不公不义而暗无天日,后者优胜,则社会方有公义与光明。于中国历史而言,孔子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通过仁学而确立起了世间的普遍性原则,并以此为尺度去衡量、重估周公奠定的礼乐体系,清除(删减)了那些不合仁学所确立的普遍性公理的礼则(比如殉葬之礼),从而把华夏伦理体系与伦理社会带进了具有普遍性基础与普遍性诉求的全新阶段。这种自觉到了普遍性原则的伦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血缘、地域与传统,因而才具有能够教化包括边疆在内的各种不同地域、不同传统、不同祖先的族群的力量,从而开辟了具有普遍(世界)史意义的东亚史。
但是,另一方面,人类的私情私利的偏执是如此顽固与强大,以致儒家那种建立在普遍伦理学基础之上的“天下为公”的普遍主义理念与情怀,一直未能驯服公共领域的家天下的冲动。直到十七世纪黄宗羲的出现,华夏思想才在孔子奠定的普遍主义伦理学基础上获得了反思和批判“家天下”的勇气与自觉。而遗憾的是,这种试图中断绵延数千年之政统的思想自觉被满清入关打断了。又得等待近三百年之后,在遭遇了西方文明的大变局下,家天下才在外力的影响下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在这过程中,华夏的仁人志士借以中断家天下的帝王政治的,则是“共和理念”。
“共和”这个词来自本土,而其理念则来自西方。在这种来自西方的“共和理念”里,新型国家有双重身份,一重是人民国家,一重是民族国家。就学理上而言,人民国家是现代国家的普遍身份,而民族国家则是现代国家的特殊身份。因为人民乃是由随身携带着普遍意志与普遍权利的成员个体组成的一个伦理群体;而民族则是由拥有特定的共同祖先、特定的共同历史传统、特定的共同文化语言以及特定的共同地域的人群组成的族群。自近代以来,也即自从现代西方文明诞生以来,无论西东,在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都既诉诸人民,也诉诸民族,而通常首先就诉诸民族。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包含着祖先、历史、文化、语言、地域等等因素在内的民族身份是每个人的显性身份。因此,在建构国家过程中,以民族为单位进行动员,是最容易获得凝聚力与认同感的。为此,近代建国者们通常都要花很大努力去唤醒民族意识,甚至去建构民族共同体。在这过程中,民族主义很自然地成为一面旗帜。
但是,民族主义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团结,但另一方面,它同时也一直隐藏着两重危险:一重是它潜藏着不断瓦解现有民族共同体的逻辑,因为一个民族单位所包含的那些要素可以通过重新叙述不断被进一步差异化为不同民族单位;一重是它的自我特殊性标识总包含着特殊性诉求、特殊性自我理解,这种特殊诉求与特殊性自我理解一旦越过理性的界限,也即越过了人类的普遍性原则,那么,它必定会把一个民族-国家带向封闭,带向狭隘,带向民族-国家层面上的私情私利的偏执。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利益与情感,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基于极端民族主义只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置人类普遍公理于不顾,只盲目自信于自己的传统与文明,无视乃至排斥其他文明,那么,它唯一的结局就是灾难。自近代以来,在世界不同地方,都有国家演绎着同样的民族主义灾难。而这样的危险在今天仍存在于世界的不同地方。要防患或阻止这种民族主义灾难,人类仍然需要一种君子文化,君子精神,君子理念,那就是明觉天下普遍之公理,信守人类普遍之正义。
在这个意义上,张丰乾先生重提君子问题,乃是一个真问题。这里,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自遭遇西方文明以来,要真正走出大变局,要防止极端民族主义与文化义和团,必以明辩古今之变为前提。如果说重塑华夏文明的君子文化能有助于今天之处境,同样也必在这一前提下才是可能的。
最后,我想提及的是,张丰乾先生在书里花了很重要的篇幅分别记录了他与两位海外学者余英时、杜维明的交往和交流。这里之所以要提及,是因为这两位海外学者很具代表性。按我们前面的划分,余先生应归于“明变派”,而杜先生则属于“温情派”。余先生的作品与其言行表明,他对古今之变有一种明确而坚定的觉悟,因此也生出了一种决绝的态度。然而,有趣的是,恰是基于其对古今之变的深度自觉,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所呈现出来的,才既显客观,又透出真切的温情。而其绝决之态度不仅体现了现代学者为学术而学术的志业精神,亦贴近了谋道不谋禄的君子风范。
书里提到另一位学者杜先生也是一位可贵的现代学者,一位值得尊敬的真正学者。这里之所以把他归为“温情派”,与他对现代性的研究和主张相关。他曾着力于对东亚现代化的研究,并提出了有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乃至不同的现代化模式的主张,而东亚就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现代化模式。这种研究与主张,在我看来,显然是出于类似钱穆先生温情先行而结出的果子。这种温情先行的现代性研究,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弱化甚至丢失对现代性社会之为现代性社会之根本处、要害处的明确认识,以致模糊乃至忽略现代性社会之为现代社会所应具有的普遍性根基与普遍性标准。这种“不同模式”说在理论上的危险带来实践上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对东亚现代性的研究不是促进了东亚社会的现代化,相反,倒为妨碍东亚社会现代化甚至反现代化提供了理由。这当然有违杜先生初衷,一定也是他所不愿看到的。这表明,对现代性的研究如果不是为了反对现代性,那么,不应是“温情“先行,而应“明变”先行。
我甚至要说,对华夏文明乃至对任何文明,唯明变,方能温情。
2021年7月31日
于学清苑